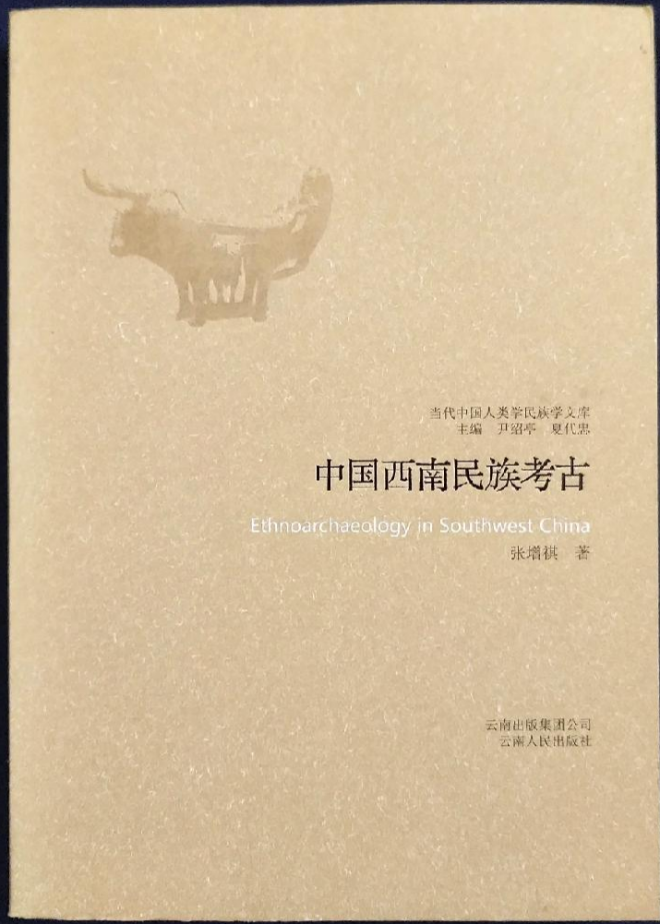
张增祺先生的《中国西南民族考古》(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初版,2010年再版)
作者:潘扬淳
“考古学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云南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自古以来便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区域。因此,有别于陕西、河南等内地各省的考古工作,云南地区的考古工作展开,不仅需对出土文物进行断代与分类,还需识别文物的族属,进而推进地区古代民族的相关研究。
云南省著名考古学家张增祺先生的《中国西南民族考古》(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初版,2010年再版),以考古学的相关材料为基础,结合历代文献载记,图文并茂地对云南地区的古代民族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是西南边疆地区“民族考古”学领域的开创之作,入选了“当代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文库”。
张增祺先生在长期的西南民族考古实践中,注意到云南各地的出土文物是由不同族属的古代先民所创造。为了明晰云南出土文物的具体族属,明确云南古代民族的族源、族系考察的实物依据,必须将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多学科有机结合,开展分析。对此,张增祺创作了《中国西南民族考古》,不仅是张先生在相关领域研究成果的集合,也是将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引入我国西南地区的开创性研究,既丰富了我国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研究,也对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张增祺先生之前,云南的考古工作已取得不少阶段性成果,但未能引起民族史学界的足够重视。鉴此认识,张先生在学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考古材料,指出云南地区的古代民族并不受后世政区分界的限制。由此,即应将古代民族的相关问题,放眼于全国乃至亚洲的高度上去分析与考察,这种理念在当时无疑是先进的。
同时该书在研究云南古代民族时,常将各族群的相关研究放到中国和亚洲的视野去考察。不单是“摩沙夷”的相关问题如此,关于云南地区动物纹饰与中亚草原地区的文化遗迹对比,以及关于战国至西汉时期滇池区域文物的西亚属性的考察等,皆是如此。这些探讨,不仅证明了云南地区古代民族与国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民族间存在密切联系,也揭示了云南与境外区域存在着频繁的贸易交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充分结合当时国际学界的研究成果,对石寨山与越南东山两种青铜文化的元素做了初步的分析论证,不仅指出越南原有土著青铜文化与包括云南在内的中国西南地区的青铜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还有力驳斥了当时在越南学界中甚嚣尘上的“铜鼓文化起源论”,明确指出云南西部地区的铜鼓文化不仅时代与器形更早,且与越南的东山铜鼓文化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这无疑是我国学界在相关领域的研究的重要嚆矢。
《中国西南民族考古》的一系列研究表明,在缺少文献资料的西南地区,许多基于传世文献得出的结论难以得到进一步印证,缺乏准确性。因此,时代相近的出土文物往往可以作为文献记载的印证,有利于相关问题的揭示与解决。虽然囿于时代背景,该书对于出土文物所具有的“补史之缺”“证史之误”的功能发挥有限,对一些问题的考察仍然仅能依靠传世文献资料来完成,但其所具有的跨地区、跨学科、跨领域的广阔学术视野和敏锐的论证思维,仍无可争议的推动了西南地区民族学和历史学的发展,为民族考古学提供了最基本、最重要的研究路径与研究方法。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