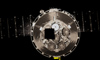最初被《鼠药》吸引的是它的形式:完全以书信体写就,上部夹杂了一些编者荆歌的评注、注和按语,下部连评注也没有了,仅有数的几条注。其次吸引我的是小说关涉到的年代,上部标示的是“一九七零年代”,下部自然就是“一九八零年代”了。我此前并不了解荆歌及其创作,我只是想看看,以书信形式呈现出来的70年代、80年代会是怎样的。就书信体所呈现的在长篇小说写作中的实验来说,我的阅读期待基本实现了,而且,某些地方还超出了我的预期,一定程度上说,这是作者在形式创新上的动力的体现,但后者却几乎不在我的期待视野之中,也就是说,我扑了个空。
书信体当然不是荆歌的创造,毋宁说荆歌实际上试图复活这一早就没落的形式。有一定文学史知识准备的读者当然都知道,书信体小说乃是欧洲文学传统,早期有名的如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卢梭《新爱洛绮丝》、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等均是传世佳构,而且都是长篇。西方小说叙事模式传入东土始于晚清,书信体也在民初出现,至五四则有庐隐、淦女士等人的实践。一般而言,形式创新的动力来自于内容的需要。就五四时期而言,书信体的形式无疑源自倾诉的要求,然而,也正因此,书信体的小说写作被后来的批评家指斥为感伤主义、文艺腔,于是书信体也便渐渐地衰落了。至新时期,虽偶有尝试,毕竟是明日黄花,早已失却了吸引人的魅力。值得一提的是,在将近百多年的汉语小说史上,似乎没有一部书信体的长篇小说。汉语文学原本长于抒情,倘使抒情是欧洲书信体小说传统的正宗,何以汉语文学不能以已之长,在抒情的书信体上出现长篇的构制呢,是力有不逮,还是另有原因?
所以,当我看到荆歌竟然以书信体写成了一部长篇,自然会有颇为强烈的期待。
就作为一种文体的书信来说,更准确地讲,是中国文类范畴中的、作为散文的书信,最要紧的是“直抒胸臆”,因其比较可靠的真实性,常以史料视之。有意思的是,其实在书信中,客观的叙事和主观的抒情并存,但大多数史家却并不对此作区分。而当书信作为小说写作的体式,其中的问题,或者说其间的张力也就毕显无遗了。可是《鼠药》不仅保留了书信体的这一特点,荆歌甚至更进一步地在文本中增强两者间的张力,或者说是一种矛盾。
小说的开篇是标示为“荆歌按”字样的几节文字。它既是个引子,却也在做着歌德、卢梭们在同类作品的开头所做过的事,告诉我们后面的这些书信都是实实在在的“信件”,即便信中的内容有假,可写信的人均实有其人。略有不同的是,歌德说,他不过是个“搜集者”,而卢梭强调的是,他既是搜集者,也是撰写者,所以是“编纂和出版者让-雅克·卢梭”。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举这些,是试图在今天的书信体写作与十八世纪的写作之间做一点比较。单从歌德的交待、卢梭的序言和荆歌的按语,还是可以看出明显的不同来。在对信件真实性的强调上,他们差不多是一致的,可我要说的是态度和目的。
在荆歌的叙述中,首先是这些信件来自于一个收废品的老头,而且是个“狡猾的老头”,甚至有些“贪婪”,他竟然向一直对他不薄的荆歌要钱。“钱”的出场已经使两者产生了很大的差别。当然,最终老头为了继续在这里得到“废旧报刊杂志”,“决定不要报酬”,可当荆歌当晚仔细看了这些信件后,发现这是“一个与爱、恨、背叛和谋杀有关的故事”,“只要将这些信件加以整理,并进行适当编辑,是完全可以成为一部别致的长篇小说的。”也就是说,如果“荆歌按”的文字是真实的,那么放在我们面前的这部小说的作者显然不是荆歌,而是邹峰等人,最要紧的是那个被指为“贪婪的”老头显然也是有功的,是付出了劳动的,他似乎理应得到属于他的那一份报酬——小说出版后的稿酬或版税。荆歌充其量只是一个类似于卢梭的“编纂和出版者”。当然,这里我们需要特别强调,我这样分析并非是要批评作者荆歌的职业道德,我们需要辨明作为作者和编注者这两种身份。也就是说,从身份的含混走向态度的暧昧,两者是显然不同的,甚至我们还可以更加严厉点说,作者看似在场,实际上却并不在场,作者已经从写作中抽身而退,变为一个地道的编辑。此其一。其二,歌德、卢梭的小说就其目的和方向而言,显然关乎启蒙、爱情、平等等现在被斥为“大词”的主题,而这部《鼠药》虽然其中依然有爱的成分,但就其主体,甚至我们可以更加直接地说,是关于“恨、背叛和谋杀的故事”,这一点无疑是对书信体主题的一个重大颠覆。这一颠覆毫无疑问与我们时代的文学阅读现状有关。
但小说家荆歌对书信体的颠覆并没有到此为止。在上部,编者荆歌常常以评注和按语、注释的形式闪身而出,或解释一些对四十岁左右的读者无须解释的现象和概念,诸如“上山下乡”的政策、粮票等票证的发行、游街陪斗等,就此而言,荆歌实际上预设了一个读者对象(或许称消费对象更合适),即对70年代的中国社会缺乏起码了解的70年代后出生的人群,而这一点恰好与对“大词”的取舍和好恶直接相关。这是很有意味的一个地方。
同时,评注还会对信件中所叙述的事情、情感的真伪做评判。这一判断多出现在上部,如对邹峰以及邹善的为人、性格、心理等均有断语,指出他们哪些信、哪些事情说谎了,甚至邹善的有心机等等。说谎既意味着欺骗的禀性,但在书信体的小说写作中则意味着所叙之事和所发之情的不真实。正是在这一点上,荆歌真正的意图显露出来了。一方面,他要借此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黑暗和卑鄙,甚至歹毒,而在文体的层面上则彻底颠覆书信体的真实性,使真与假缠挟在一起;而且,集中表现邹善与其嫂不伦之恋的下部在上部的反照中显得真真假假,真假莫辨,尤其是邹善在信中所表现出来的对苏惠“炽烈”而畸形的爱欲更令人欲迎还拒、莫衷一是。换言之,人物奸诈、虚伪、狠毒等等的性格因素与文本在形式上的真假难辨构成了一个潜在的紧张关系,互相牵制,在彼此矛盾、否定的关系中却又互相阐释、说明,或者反过来同样可以成立。
所以,在《鼠药》中,书信体这样一种包含隐秘、真实性的文体被小说作者在形式创新上的用心和书信作者(小说作者的虚构)在性格、气质方面的虚伪心机彻底改变了,邹善们在倾诉的同时,也在泄露着人心险恶的秘密,而人心的险恶就以不断出现的“鼠药”得以充分的揭示。所以,与其说《鼠药》要表达的是传统书信体惯于表达的“倾诉”,不如说其根本目的在“揭示”,揭示人心和人性的阴暗和恶毒。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荆歌选取70-80年代为其背景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揭示这一点。可要紧的是,小说上部对文革的叙述与对邹善兄弟,特别是他们父母的呈现基本上是脱节的,两者并没有构成一种因与果的关系,邹父的暴戾、乖张和邹母深藏不露的对其父的大恨(她竟然长期给其夫服食鼠药,因量少而不易发作,最终死于每况愈下的健康)与那个时代并无必然的关联,且小说中其它人物的命运也很难断定就是时代的结果和悲剧。也就是说,荆歌实际上只是将这个时间段作为一个道具,一个为了真实性而使用的时间概念,一个被抽空了具体历史性的时间场域,其根本目的乃是为了揭示上述所谓普遍的人性。这一点可以从下部对于真相、死亡等问题的讨论得到印证。也可以说,如果上部尚有一些对于具体历史性的呈现,即便那呈现也带上了较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色彩,而下部却越来越偏离这一方向,将重心放在对普遍人性的揭示上了。而这一点恰恰是80年代中期兴起的先锋派文学的局限所在,说白了,也是我的不满所在。在我看来,无论如何,对于荆歌这样一位出生于1960年的小说家来说,这是一个损失。(郭春林)





①云南日报报业集团授权云南网,在互联网上使用、发布、交流集团10报4刊的新闻信息。未经本网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或利用其它方式使用云南日报报业集团任何作品。已经本网授权使用作品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并注明“来源:云南网”或“来源:云南网-云南””。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②凡本网注明“来源:云南网”的作品,系由本网自行采编,版权属云南网。未经本网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或利用其它方式使用。已经本网授权使用作品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并注明“来源:云南网”。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方式: 0871-4156534
附:云南日报报业集团10报4刊:云南日报 春城晚报 云南经济日报 影响力 滇池晨报 云南法制报 大众消费报 文摘周刊 东陆时报 社会主义论坛 车与人 民族时报 云南科技报 大观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