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万年回响 漫说“上山”——《上山——中华文明的万年奠基》评析

彩陶壶形罐(桥头遗址) 图片由作者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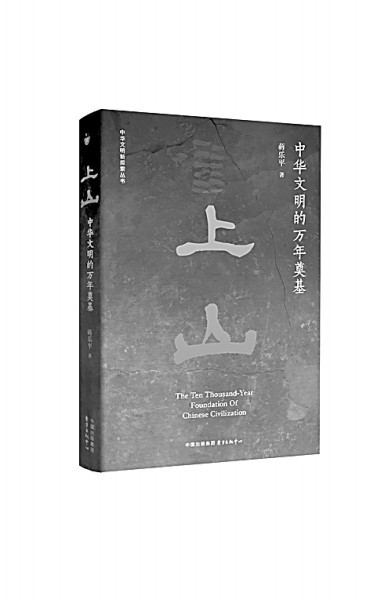
图片由作者提供

太阳纹彩陶片 图片由作者提供

上山遗址发现的距今10000年的炭化稻米 图片由作者提供

上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图片由作者提供
上山文化作为21世纪初才渐露真容的史前遗珍,闪耀着最早的稻作农耕曙光,回荡着人类从狩猎采集向定居农业过渡的最初跫音。面对这一重要的考古发现,其价值与内涵亟待系统而简明的梳理。尤其在上山文化遗址群已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背景下,全面、准确且生动地解读其意义显得尤为重要。《上山——中华文明的万年奠基》(以下简称《上山》)一书的使命,正是拂去历史尘埃,彰显上山文化在中国及世界文明史上的独特地位。
稻源初现 农业革命的“万年样本”
《上山》(东方出版中心,2025年)一书的核心使命,在于完整地揭示上山文化为何能成为中华文明的“万年奠基”——它具体奠定了哪些基石,并阐明这些早期成就如何为后续的文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奠基”地位的论证,是全书立论的根本,必须建立在严谨的学术研究之上。
本书在谋篇布局之中,始终秉持着一条清晰的逻辑阐述路线,即以考古实证为基础,揭示上山文化的深厚底蕴。这条逻辑链的每一环节,都紧紧围绕一个核心要素,即“价值”。上山文化的价值,首先体现在它为我们提供了世界稻作农业起源的“万年样本”。
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在其经典的关于“农业革命”的论述中,认为农业起源是文明形成的开始。既然称之为“革命”,就必须展现出与之匹配的、具有颠覆性的成果。这一成果,如能由一种既有确凿考古学内涵,又拥有一定时间跨度可供深入观察与研究的考古学文化集中体现,无疑最为理想。上山文化正是这样一个能够充分展现稻作农业起源阶段革命性成果的“万年样本”。
距今约一万年的上山遗址,并非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甚至也不是最早发现零星水稻遗存的地点。在人类早期探索农业的漫长过程中,可能存在多地点的多次尝试。然而许多早期尝试如“昙花一现”,未能持续发展。而上山文化所代表的稻作农业探索,却成功“开花结果”,展现出稳定的发展态势,为最终孕育出更高级的文明形态打下基础。
目前发现的上山文化遗址已有24处,是早期农业遗址中规模最大、分布最密集的遗址群。说明在稻作农业这一新的生计模式支撑下,上山先民获得了持续的食物来源保障,人口得以稳定增长,社会规模得以扩大和发展。没有成功的农业作为基础,如此规模的聚落群是难以想象的。这正是农业革命带来人口增长和社会复杂化的直接体现。
上山遗址群所描绘的这幅东方世界万年前的稻作农业图景,对绝大多数当代人而言,既熟悉又陌生。熟悉在于,稻米至今仍是我们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主食;陌生在于,我们很难想象万年前的先民,在没有金属工具、没有系统历法的情况下,是如何凭借原始智慧与惊人毅力,开启驯化野生稻、耕耘土地的伟大创举。这份陌生与新奇,恰是上山文化最迷人之处。它挑战我们对“原始”与“文明”的刻板印象,迫使我们重新审视人类文明的起点。它以不容置疑的姿态告诉世界:在遥远的东方、在长江下游这片土地上,万年前的先民早已点燃农业文明的星星之火。
旷野跫音 跨越时代的变革象征
当我们深入探讨上山文化的历史地位时,仅将其限定于碳十四测年数据所框定的“万年”时间框架内,是不充分的。诚然,这些精确的年代数据提供了科学的坐标,让我们得以使用具体的数字定位上山。但更为重要的是,上山文化所蕴含的时代意义,其对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揭示,远超出数字本身。它的时代性,可象征性地表述为人类社会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洞穴为主要栖居方式,向新石器时代早期走向开阔平原、构筑聚落的伟大转折。这不仅是居住空间的迁移,更是生产方式与社会组织的深刻变革。
要理解这一转变的性质,有必要引入“原生”与“续生”的概念。
所谓“原生阶段”,通常指直接在旧石器时代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早期新石器文化类型。在文化堆积上,“原生阶段”的遗址往往直接叠压于旧石器文化层之上。华南地区发现的诸多洞穴遗址,便是这一阶段的典型代表。
而“续生阶段”,通常晚于“原生阶段”,但并非其简单延续。“续生阶段”最显著的特征,是人类群体开始主动、大规模地脱离旧石器时代以洞穴为中心的生存环境,走向更广阔的旷野地带。在这些新地理单元上,农业生产生活模式开始初步显现并逐渐占据主导。长江中下游的早期新石器文化,如上山文化,正是“续生阶段”的代表。与这一转变相适应的,自然包括器物形态的直接变化。以夹炭红衣陶为显著特征的制陶工艺在长江流域的出现及其全新陶器群,正是上山文化的典型体现。
从考古学观察,华南洞穴类型虽比长江中下游类型的发生时间更早,但二者的演进轨迹呈现平行发展的态势,不宜简单归纳为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相较于线性演进模型,从“原生”与“续生”两种不同发展路径与模式的角度进行分析,更能揭示其内在差异与联系。“原生阶段”必然对“续生阶段”的产生与发展施加影响,但后者代表了更具革命性的突破。
若将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作为稻作农业起源的考察对象,就必须将洞庭湖周围的彭头山文化视为“续生”文化的重要一支。将两者进行比较,并非出于孰先孰后的狭隘地域之争,而是为更好梳理该区域稻作农业早期发展的文化关系。从长江中下游早期新石器文化自身演进序列分析,彭头山文化可能是上山文化向跨湖桥文化过渡的促进因素之一。
书中关于“原生”与“续生”的辨析,以及将上山文化置于长江中下游乃至更广阔史前文化背景下的比较研究,其核心目的,正是为凸显“从洞穴到旷野”这一转变的划时代意义。这不仅是居住地的选择,更是生存策略、技术体系、社会结构乃至精神世界的全面革新。上山文化以其在“续生阶段”的先锋地位,生动诠释了人类如何主动适应环境、改造自然,并最终迈出走向农耕文明的关键一步。
文明基因 从上山到良渚的传承之路
彩陶是上山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特征之一。此项工艺由早期的夹炭红衣陶逐渐演变而来;到了中期,开始在罐、壶、盆等部分器物上出现红色与乳白色的彩绘纹样,如太阳纹、平行线纹、点彩纹等。这些纹饰虽略显粗犷,不及后世彩陶文化那般成熟精细,却无疑标志着上山先民在制陶技艺与审美意识上的重要突破。彩陶不仅是对实用器物的美化,更是早期精神信仰与艺术追求的物质见证。
更为引人注目且充满想象空间的,是义乌桥头遗址出土陶器上的“卦形符”。这些符号有的形似后世八卦中的“豫卦”,有的呈现不同组合形态。尽管目前尚不能断言其具体表意功能,但它们表明,上山时期的先民已开始尝试用抽象符号系统表达特定观念或信息。若将这批符号与年代稍晚的跨湖桥文化遗址中出土的、更为成熟和系统化的刻划符号体系相对比,似乎可以勾勒出一条早期符号发展演化的轨迹。
因此,书中强调了太湖以南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中的关键作用。上山文化所开创的稻作农业传统,为后续区域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经济基础。没有稳定的农业生产提供持续食物保障,就不可能有富余劳动力从事手工业生产,更难以形成复杂的社会组织结构。有充分证据表明,后来兴起于钱塘江流域及太湖周边的、高度发达的良渚古国,其源头正可追溯至以上山文化为代表、在此地延续数千年的农耕文明传统。上山文化的种子,在万年前的旷野中生根发芽,最终长成良渚这棵参天大树。这一文明演进的脉络及其内在的文化基因传承,清晰而有力,不容忽视。
《上山》一书的价值,不仅在于重现一段遥远的史前历史,更在于通过对上山文化的研究与阐释,让读者更深刻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上山文化所展现的,不仅是稻作的起源、彩陶的发明、村落的雏形,更是人类永不止歇的探索精神,以及对美好生活最本真、最执着的向往。这种精神的力量,足以跨越万年时空,依然与今天的我们深深共鸣。
(作者:蒋乐平 韩泽玉,分别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上山文化遗址主要发现者;金华市上山文化遗址管理中心助理馆员)(蒋乐平 韩泽玉)


